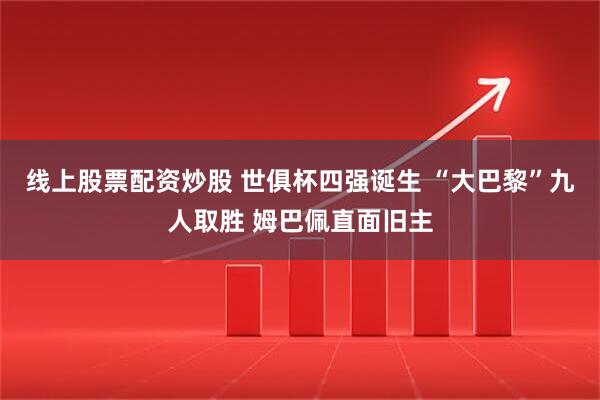01线上股票配资炒股
那年我十九岁,是1987年的夏天。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,我就回了我们靠山屯,在村小学当了个民办教师,一个月挣三十块钱,勉强糊口。那会儿的农村,十九岁的小伙子,要是家里没门路,这辈子基本就算看到头了。
可我心里,还憋着一股劲儿。我想再考一次,考出去,看看山外面的世界。这事儿,我谁也没告诉,就怕人家笑话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
我们学校,那年春天从县城里调来一个女老师,叫沈静。她二十四五岁的样子,是正经师范毕业的,来我们这儿支教。她跟我们屯里的姑娘不一样,说话声音细细的,走路腰板挺得笔直,总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裙子,身上有股淡淡的墨水香。她长得好看,是那种书里说的“娴静”的好看,平时不怎么笑,可一笑起来,眼睛就像弯弯的月牙,能把人的魂儿都勾走。
屯里的大小伙子们,都偷偷叫她“月牙儿老师”,可谁也不敢往前凑。她太干净了,干净得像天上的云,我们都是地里的泥,只敢远远地看着。
那天晚上,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。豆大的雨点子砸在房顶的瓦片上,“噼里啪啦”地响,跟要拆房子似的。放学后,学生们都让家里人接走了,就剩下我和沈老师。她家在村子最东头,是以前生产队的一个旧仓库改的,离学校最远,中间还得过一条泥泞的大土路。
展开剩余91%“沈老师,雨太大了,我送您回去吧。”我看着窗外电闪雷鸣的,心里不放心。
她犹豫了一下,还是点了点头。我找了把破油纸伞,我俩就这么一头扎进了风雨里。那条路,晴天都坑坑洼洼的,这会儿更是成了一条烂泥河。伞根本不管用,我俩没走几步就浑身湿透了。好几次,她都差点滑倒,是我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,才没让她摔进泥坑里。
她的胳膊很细,隔着湿透的衣裳,我能感觉到微微的凉意和颤抖。我一个十九岁的毛头小子,哪跟姑娘家这么近过,一张脸烧得比天上的闪电还亮。
好不容易,深一脚浅一脚地把她送到了家门口。那是个孤零零的小院子,在风雨里显得特别萧瑟。我把伞收了,正准备告辞,她却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。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她堵在门口,没让我走。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淌,几缕湿发贴在她苍白的脸颊上,那双亮晶晶的眼睛,在昏
黄的灯光下,显得格外明亮,也格外……让人心慌。
然后,她就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、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语气,重复了一遍。
“雨这么大,回不去了。”她说,嘴角竟然勾起一抹浅浅的笑,“老师……给你单独辅导一晚。”
02
我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,像被雷劈了,浑身上下的血都往脸上涌。
“单独辅导”……
我一个十九岁的后生,血气方刚的,哪里经得住这种话的撩拨。尤其这话,还是从我心里敬若神明的沈老师嘴里说出来的。我的心,跳得跟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。我甚至能感觉到,我那身湿透了的廉价衬衫,底下起了密密麻麻一层鸡皮疙瘩。
是……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?
我不敢看她的眼睛,只能盯着自己滴着水的裤脚,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。我想到屯里那些老光棍们晚上凑在场院上说的荤话,想到画本子上那些不清不楚的男女之事……难道,沈老师她……
“你……你瞎想什么呢?”
就在我胡思乱想,快要原地爆炸的时候,她突然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,声音清脆得像山泉水滴在石头上。她抬起手,用手背轻轻敲了一下我的额头。
“你这脑袋瓜里,除了浆糊,就是草稿纸吧?”她嗔怪地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,不像老师看学生,倒像姐姐看一个不懂事的弟弟。
她说着,侧身让我进了屋。
“把你那些旧课本和练习册,都拿出来。”她指了指屋角那张掉漆的木桌,“我前几天去你宿舍,帮你晒被子的时候看见了。你小子,藏得够深的啊,还想再考一次,嗯?”
我愣住了,像个做坏事被当场抓住的孩子,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。原来……原来她早就知道了!
我这才明白,她说的“单独辅导”,是真真正正的辅导!辅导我考大学!
那一刻,我心里那点龌龊的、旖旎的念头,瞬间被一股巨大的羞愧和感动给冲得一干二净。我为自己刚才的胡思乱想,感到无地自容。
“沈老师,我……”我结结巴巴地,想解释,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
“行了,别我呀我的了。”她把一盏煤油灯点着,昏黄的灯光,一下子就把这间简陋的小屋照得暖烘烘的。“快去把湿衣服换了,我给你找身我弟弟以前的旧衣服。然后,咱们就开始。时间可不多了。”
我看着她,这个在暴雨夜里,为我点亮一盏灯的女人。我的眼睛,一下子就湿了。我知道,这盏灯,可能会照亮我剩下的一辈子。
03
那一晚,成了我生命中最深刻的记忆。
窗外是瓢泼大雨,电闪雷鸣。屋里,是摇曳的煤油灯火,和沈老师温和的讲课声。我换上了她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一套旧中山装,虽然有点大,但干爽温暖。我们俩就坐在那张小小的木桌两端,她拿着我的旧课本,一道题一道题地给我讲。
她的声音真好听,像收音机里播音员的声音,不急不躁,再复杂的公式和定理,从她嘴里说出来,都变得清晰易懂。我这才知道,我以前自己埋头苦读,走了多少弯路。
灯光下,她的脸庞显得格外柔和。雨水打湿的头发还没干透,贴在脸颊上,让她少了几分平时的清冷,多了几分说不出的温柔。讲到一道难题,我还是不懂,她就凑过来,拿起我的笔,在草稿纸上一笔一划地演算。她的头发,有几缕不小心垂落下来,轻轻地扫过我的手背,痒痒的,也让我的心,跟着痒痒的。
我不敢抬头,只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墨水香,混着雨后青草的味道。那一刻,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,该有多好。
我们一直学到后半夜,直到煤油灯里的油都快烧干了,我才趴在桌子上,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
我做了一个梦。我梦见自己考上了大学,坐上了去往山外面的火车。火车开动的时候,我回头看,看见沈老师就站在月台上,穿着那条蓝布裙子,对我微笑着挥手。
从那天起,“单独辅导”就成了我和她之间的一个秘密。
每天晚上,等学生们都走光了,我就会悄悄地跑到她的宿舍。她会为我点亮那盏煤油灯,然后,我们就在那方小小的天地里,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。她把她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,托人从县城里,给我买回来一大堆崭新的复习资料。那些书,在当时的我看来,比黄金还珍贵。
我们的关系,也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“看见没,那陈家小子,天天晚上往沈老师屋里钻,一待就是大半夜。”
“哼,一个黄毛丫头,一个半大小子,孤男寡女的,能有啥好事?”
流言蜚语,像刀子一样,扎得我心里生疼。我怕,我怕这些脏水,会泼到沈老师那身干净的蓝布裙子上。
04
我好几次跟沈老师说,要不算了吧,白天在学校补习也一样。
可她总是摇摇头,眼神很坚定:“白天你要上课,我也要上课。只有晚上,才是你自己的时间。陈默,”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,“嘴长在别人身上,路,在你自己脚下。你要是连这点闲话都扛不住,以后还怎么去走更远的路?”
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。是啊,跟考上大学,走出这座大山比起来,这点流言蜚语又算得了什么?
我把所有的委屈和精力,都化作了学习的动力。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,疯狂地吸收着她教给我的所有知识。
一个深秋的夜晚,我们又在补习。我无意中看到,她桌子的玻璃板底下,压着一张照片。照片上,是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男人,穿着海魂衫,笑得一脸灿烂。
“这是……你对象吗?”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。
她正在给我讲题,听到我的话,手里的笔,微微一顿。她沉默了很久,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。她才轻轻地点了点头,眼神一下子就黯淡了下来,像是蒙上了一层雾。
“他叫林海,”她轻声说,像是在对自己说,“是个海军。我们……本来去年就该结婚了。”
我心里一紧,追问道:“那……他人呢?”
她没有回答我,只是拿起那张照片,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那个男人的脸庞。过了好一会儿,我才看到,一滴晶莹的泪珠,从她眼角滑落,滴在了照片上。
“他……他为了救落水的战友,再也没回来。”
我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,像被重锤狠狠地敲了一下。我呆呆地看着她,看着这个平时在我们面前那么坚强、那么沉静的老师,在这一刻,露出了她最脆弱的一面。我这才明白,她那双像月牙儿一样好看的眼睛里,为什么总藏着一丝化不开的忧伤。
“我来这里支教,也是因为他。”她擦干眼泪,对我勉强笑了笑,“他总说,他想等退伍了,就去最偏远的山区当老师,让那里的孩子也能看见大海。他没能完成的心愿,我替他来完成。”
她顿了顿,抬起头,看着我,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灼热的光。
“陈默,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吗?”她说,“因为我从你身上,看到了他当年的影子。一样的倔,一样的穷,一样的不认命。他常说,读书,是你们这些山里孩子,唯一能改变命运的路。我不能让他失望,也不能……让你失望。”
那一刻,我再也忍不住,眼泪夺眶而出。我一个十九岁的男子汉,在她面前,哭得像个孩子。
05
时间,就在煤油灯的燃烧和粉笔的摩擦中,飞快地流逝。
转眼,就到了第二年夏天,高考的日子。
去县城考试的前一天晚上,沈老师没有再给我补课。她破天荒地,炒了两个菜,一个青椒炒肉,一个西红柿炒蛋。她说,这是状元餐,吃了就能考中。
那顿饭,我们俩吃得很慢,也很安静。谁也没说话,但彼此心里都清楚,这顿饭,也是我们的散伙饭。考完试,无论结果如何,我都会去走我自己的路,而她,支教期满了,也要回到属于她的城市。
我们的人生,就像两条相交的线,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有过短暂的重合,然后,就要各自奔向不同的远方。
临走时,她送我到门口。月光下,她的身影被拉得很长。她递给我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。
“这里面,是两支新钢笔,还有十块钱。到了县城,别舍不得住店,也别舍不得吃饭。把身体养好了,才能打仗。”
我攥着那个还带着她体温的手帕包,感觉有千斤重。我看着她,想说声谢谢,可话到嘴边,却怎么也说不出口,只剩下眼圈发红。
“去吧。”她对我笑了笑,还是像以前一样,像个月牙儿,“老师,在村里等你凯旋的好消息。”
我重重地点了-点头,转身,头也不回地,走进了沉沉的夜色里。我不敢回头,我怕一回头,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了。
那三天的高考,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我写的每一个字,解的每一道题,背后都仿佛有她的目光在注视着我。
考完试回到村里,我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跑到学校去找她。可她的宿舍,已经人去楼空。桌子上,收拾得干干净净,只有那盏陪伴了我们无数个夜晚的煤油灯,还静静地立在那儿。
我问了校长,校长说,她昨天就走了。县里派车来接的。她没让任何人送,就这么悄悄地走了。
她给我留了一封信。信里,只有短短的一句话:
“陈默,祝你,前程似锦。去看那山外的大海吧,连同林海的那一份,一起看。”
我拿着那封信,站在空无一人的宿舍里,心里,一下子就空了。
0.6
放榜那天,我考上了。是我们县那年的文科状元。
我们靠山屯,出了几十年来的第一个大学生!消息传来,整个村子都沸腾了。我叔放了三挂鞭炮,请全村人吃了顿流水席。
我成了全村人的骄傲。可我心里,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我最想分享这个好消息的人,却不在我身边。
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,给她写了信,一封又一封。信里,我跟她讲我大学里的新鲜事,讲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的激动。可我的信,都像石沉大海,没有一封回信。
后来,我放假的时候,专门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,去了她信上留的那个城市。可我找到那个地址时,邻居却告诉我,那家人,早在两年前就搬走了,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
从那以后,沈静,这个在我生命中留下最深刻印记的女人,就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。
大学毕业后,我留在了城市,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,后来还成了家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我的人生,真的像她祝愿的那样,前程似锦。
可我心里,始终有一个结。我时常会想起1987年的那个暴雨夜,想起她堵在门口,对我说的那句话。那句话,就像一道光,劈开了我混沌的青春,照亮了我未来所有的路。
我欠她一句当面的感谢。这句感谢,在我心里,一欠,就是三十年。
07
几年前,我借着一次出差的机会,回了一趟老家。
靠山屯,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了。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,土坯房变成了二层小楼。当年的村小学,也已经废弃了,成了一片荒草地。
物是人非。
我凭着记忆,找到了当年沈老师住的那个旧仓库。院墙已经塌了半边,屋子也破败不堪。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门,走了进去。
屋子里,积满了厚厚的灰尘。只有那张掉漆的木桌,还固执地立在原来的位置。
我走到桌前,用手拂去上面的灰尘。我突然发现,桌子的一个角落里,好像刻着什么字。
我凑近了,仔细地辨认。那是一行用小刀刻上去的、娟秀的小字,字迹已经很模糊了。
“林海,你看,我又找到了一个像你一样,眼里有光的孩子。”
看到那行字,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,再也控制不住,蹲在地上,嚎啕大哭。
我终于明白,她为什么不回我的信,为什么不愿意再见我。因为在她心里,我只是她对亡夫思念的一个载体。她完成了她的承诺,把我送出了大山,她也就该退场了。她不想让我的人生,背上任何关于她的、沉重的包袱。
她就像一艘渡船,把我从绝望的此岸线上股票配资炒股,渡到了希望的彼岸。船靠了岸,她就悄然离去,深藏功与名。
发布于:河南省迎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